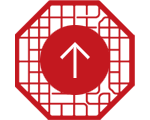十四艺节·群星璀璨 | 这就是像生活一样出彩的群众文艺
10月12日,在四川成都,来自全国各地的27个作品登上第二十届群星奖音乐终评的舞台。台上,节目各有特色;台下,不时有掌声响起。赞赏、鼓励、共鸣、思考,人们在细品群文音乐酝酿3年的这张答卷。

第二十届群星奖音乐终评现场 活动主办方供图
民族风更考验功力
清澈童声,无需过多点缀,自成天籁。随着小小的身体纵情摇摆,射箭、赛马、摔跤等那达慕经典竞技场景一一浮现……音乐终评现场,内蒙古作品《快乐那达慕》排练片段就“出了圈”。孩子们纯真而投入的表演唱,融合了呼麦、鄂尔多斯短调民歌等音乐形式,广袤无垠的草原气息扑面而来。
孩童的稚嫩、真诚与民歌的辽阔、恢宏互为补益,现代编曲手法与传统音乐底蕴融合有度,碰撞产生的感染力给人带来惊喜。
在音乐创作中,突出民族音乐特色被视为一条“捷径”。以往,无论是原生态呈现还是经典民歌改编,特有的声腔底色配合民族服饰、道具往往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。但因使用这一方式的创作者越来越多,民族风格的音乐有时也显得热闹有余、韵味不足。本届群星奖入围终评的音乐作品对此多有破解之道,在演绎中入心动情,滋味足、有性格,在生活感之上多了艺术性,体现了群文创作整体水准的可喜提升。
“拉嘎勒!舍盖勒!”频频出现在甘肃作品《白马山寨》中的这两个词表达出幸福、快乐的精神内核,将白马人耕地、除草、割麦、打墙的劳作日常唱成了诗;湖南作品《撮珠朵·嫁》中,“撮珠朵”直译为“要出嫁”,大胆采用阿卡贝拉无伴奏合唱形式,巧妙融入土家高腔、土家溜子,将土家族的哭嫁婚俗表达得完整而富有新意。
不给创作设框框
创新仍是最大焦点。“新”从哪儿来?根底和眼界,缺一不可。
演奏者将手悬在特雷门琴上方,仅靠移动手的位置,就能隔空奏出空灵音色。上海器乐重奏作品《海上·云梦》最先抓住观众注意力的,便是这件小众乐器及其特殊的演奏方式。
特雷门琴是全球首个无需身体接触弹奏的电子乐器,诞生至今有百余年历史,国内可以熟练演奏的人不多。从偶然发现这件乐器到寻找演奏者,再到为乐器定制音乐段落,《海上·云梦》作曲孙彬彬足足花了大半年时间。当特雷门琴沿着逐个音符找到与中阮、竹笛、鼓乐、大提琴等诸多乐器的融合方法,孙彬彬和演奏者所跨越的障碍已数不清。
而当西洋乐器奏出含蓄内涵的东方韵调,民族乐器奏出西洋曲风,中西、传统与现代灵活切换,《海上·云梦》得到的普遍评价是“很上海”。与以往不同,此“海”非“海派”,更倾向于赞其如大海般的开放包容。
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触发人们的思考。陕西作品《丝路回响》以传统乐器板胡、琵琶、笛等为基底,融入现代电子乐,传统乐韵与电声乐音的交织丰富而不杂乱,是多民族文化交融互鉴的成果体现。云南作品《响到一起来》汇集彝族大鼓、基诺族太阳鼓、佤族木鼓、基诺族“奇科”、佤族“口得”、彝族直笛等少数民族打击乐器和吹管乐器,各自的音色既未被湮没又和谐统一,诠释的恰恰也是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深刻内涵。贵州作品《和·苗》将黔西片区苗族独有的“江不读”(大筒箫)、“多江”(直箫)、芦笙和苗族飞歌、山歌等融合,在作品终段,“江不读”的独奏既是情感上的升华,也完成了意境的营造。
唱出生活好彩头
有专家认为,群文创作应避免像专业院团一般“内卷精致”,而要做艺术表达的“试验田”。此次参与终评的音乐作品中不乏“试验”之举,值得关注。
代表音乐终评举办地的作品《成都街头走一走》,名副其实地谱出城市进行曲。事实上,具有鲜明地域特征的音乐作品并不容易创作,难就难在如何更出彩。
凭借一步一个脚印的努力,《成都街头走一走》完成了从元素堆叠到典型提炼再到时尚编排的蜕变。几次“减法”做下来,留下的不是四川清音、变脸等惯常想到的成都艺术形式,而是小贩的叫卖声、路人的欢笑声这样的“烟火素材”,还有富有街头风格的“铜人”表演、说唱等。
该作品的演员多数为成都市文化馆自2018年以来支持和培育的成都街头艺人。他们熟悉街头,把对街头的真实的生活体验融入作品,也因此拥有了以表演还原和淬炼成都文化的能力。演员们说,当站上终评舞台,他们怀抱的是对一座现代都市的信心和责任感。
作品来自街头、描绘街头,也将回归街头,继续接受群众的打磨。这正是群文作品坚守人民立场的体现。生活有多精彩,群众文艺就有多出彩。